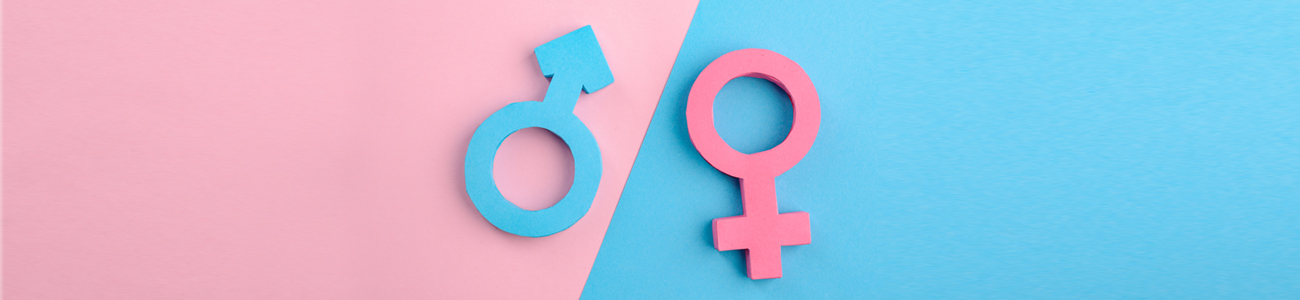文 / 陳紫吟
「雖然現在這麼說也許沒有用,可是我真的覺得,如果我們兩個那時候一直在一起,也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當我和妹妹說,在好久以前我曾經被堂哥性騷擾,然後妹妹是這麼回答的。我覺得很想哭,原來保護小孩不應該是大人的責任嗎?
我不知道那時候的妹妹年紀多小,就如同我也不確定第一次犯罪發生的時候,我的年紀有多小。但是堂哥大我七歲,他不是懵懂無知的加害者,我猜他什麼都知道。
我猜他知道,在一個傳統的大家庭裡,身為長孫的他不會犯錯;我猜他知道,因為他說了「這是我們的秘密」,所以我就真的不會說;我猜他知道,當我問他會不會對我的妹妹們做相同事情的時候,只要他回答不會我就會繼續容忍、當唯一的受害人;我猜他知道,小時候的我,太想當一個好姐姐了。
我猜這些他都知道。他大概還知道,像性騷擾這種事,只要是發的當下沒有其他人看到,加害人就能永遠安全。

他不知道的是,我在刻意遺忘這些事好多年後的某天會再次想起來,甚至說出來。只是,犯罪地點——阿嬤家的大房子、以後或許會變成他的財產的大房子
——好像被父權體制幽靈緊緊纏住,所以即使我說出來也沒關係,因為所有人都會站在他那一邊、指控我才是說謊者。他不知道我會說出事實,因為他沒必要知道。
因為是女生,所以被堂哥性騷擾;因為是女生,在被堂哥性騷擾之後,還必須忍受不知情的阿嬤不停誇獎堂哥是個很優秀的人。偶而阿嬤也誇獎我,但接下來總是要感嘆「怎麼是女生」,如此遺憾。這是我的日常性別經驗,如此遺憾。
擁有性犯罪下受害人身分的我,在成年後不小心長成了一名女性主義者,接著我想起了那些痛苦的受害經歷,同時明白,性犯罪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有加害者的存在。
「性犯罪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有加害者的存在。」
在想起來之後,我每天都要跟自己說好多遍,這樣我才不會懷疑我的爸媽有錯。在想起來第一次被侵犯大約是在小妹還小的那時候、爸媽都很忙的那時候,之後,我每天都要跟自己說好多遍:性犯罪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有加害者的存在。我的兩個妹妹都是很棒的人,他們很溫柔而且很有耐心,最重要的是,在我用極度破碎的言語向他們訴說那些我所經歷的犯罪後,他們沒有把我當作必須遠離的奇怪的人。
他們都有好的性別意識,都知道不應該檢討受害人。我的妹妹們都是很棒的人,可是身為姐姐,我覺得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