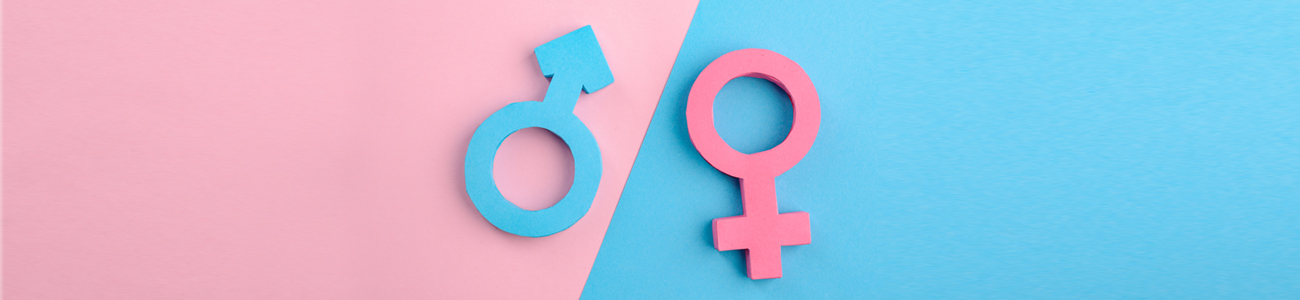女子。書櫃-好書分享
全部主題專欄
-
View More 《弒母情結:彼此控制與依存的母女戰爭》
-
View More 【性別觀查】美,不只有一個樣貌─奧運女性外表評論的反思性別的這件事【性別觀查】美,不只有一個樣貌─奧運女性外表評論的反思
每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不僅是全世界體育愛好者的盛宴,更是運動員展示自身實力與毅力的舞台。然而,在這個全球矚目的體育盛事中,女性運動員常常不僅面臨比賽壓力,還要忍受來自媒體和公眾對其外表的苛刻評論。這種現象不僅反映了對女性的性別偏見,還凸顯了社會對女性外表的固定印象,即女性應該擁有陰柔、符合傳統審美的外貌。 -
View More  月經平權做伙「來」,汙名貧窮攏總「洗」-關於月經的那些事月經平權
月經平權做伙「來」,汙名貧窮攏總「洗」-關於月經的那些事月經平權月經平權做伙「來」,汙名貧窮攏總「洗」-關於月經的那些事
我們希望,每一個正在經歷月經的女性,
都能被這個社會溫柔的對待。
女生出生時,卵巢內已有數百萬枚未成熟的卵子。
踏入青春期,在荷爾蒙的刺激下,每月約有數十枚卵子開始成長。
在一般情況下,每次只會有一枚卵子成熟,並排出子宮(稱為排卵)預備受孕。
與此同時,子宮內膜為懷孕作準備而增厚。
如卵子沒有受精,便會連同增厚的組織,通過陰道排出體外,這就是經血。
「月經貧窮」指的是人們因為無法負擔、或缺乏可取得生理用品資源的管道,
以至於月經來潮時,必須不正常的減少使用數量,
或使用其他物品,如襪子、樹皮、衛生紙等等來替代,
進而導致陰部重複感染、陰道炎、骨盆炎、不孕、子宮頸癌等生理影響,
及嚴重憂鬱、焦慮等負面心理健康影響的一種社會現象。
全球有8億以上女性人口,正在經歷嚴重的月經貧窮
在英國,有14萬以上的學生因月經貧窮而曠課
有88%的印度女性只能使用破布、甘草灰等替代正常生理用品
在臺灣,有許多家庭必須在麵包與生理用品之間作抉擇
泛指任何因爲月經而產生的社會禁忌,與其衍生的避諱風氣和羞辱行為。
其中包含將月經視為不潔的、羞恥的事,或是將月經視為不得於公開場域談論的話題,
以及生理女性在經期時不得參與宗教儀式與習俗的原因等等。
月經不平等
月經不平等(Period Equity)泛指人們因為受到月經這一項特定生理性別獨有的先天生理現象影響,
而在不同層面產生不平等的狀況,甚至因此造成部分原先就身處弱勢的人,
其弱勢情形更加惡化的現象。
月經不平等所涉及的範疇十分廣泛,
時常被討論的包含生理用品稅、公共場域是否提供生理用品、生理假等。
月經不平等背後,看見的不只是社會問題、貧窮問題,
更顯現了制度中性別不平等、權益被忽視等問題。
整體社會對月經相關教育、知識的缺乏與不重視權益,皆加深了月經不平等的現象。
從現在起,你我的加入,讓「月經不平等」有無限翻轉的可能!
【掃描或點擊QR-code即可進入申請表單】
在推動月經平權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相信有了你我的支持與認同
這個世界能夠給予月經更多尊重與友善
我們都不再為月經所困
以上資料參考自: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
-
View More 【在土地根脈中的藝術】中寮之藝─小也創辦人綠色經濟×藝術特展【在土地根脈中的藝術】中寮之藝─小也創辦人
2020年,小也與夥伴們創辦了「中寮之藝」工作室,
看到了人口外移嚴重的中寮,小也與夥伴們決定用工藝教育的方式,
為在地的年輕學子及婦女,創造職涯發展的機會,點亮他們的未來。
延續爺爺奶奶教育的初衷,帶領學生們從採集、敲打,到工藝品的製作,
認識南島樹皮的文化與歷史,並創造樹皮工藝微型產業,
也吸引了學生們的媽媽一同加入。
中寮之藝不僅提供在地學子、婦女學習技藝及紓壓的空間,
創作的工藝作品,也能作為商品販售,創造環保永續的綠色經濟,
為地方帶來技藝創新、人才培育,創造青年和婦女的就業機會。 -
View More 【綠能永續 磐石心靈】碧峰社區─楊玉平執行長綠色經濟×藝術特展【綠能永續 磐石心靈】碧峰社區─楊玉平執行長
楊玉平執行長自105年加入碧峰社區環保志工隊,
帶領碧峰社區從做資源回收,到建立起綠色經濟的善循環。
除了將資源回收的收入回饋到社區,支持長照服務、打造優良的社區環境,
更與地方產業結合,創建一套讓社區能夠自給自足的綠能永續發展系統。
透過身體力行的方式,執行長希望讓更多人了解碧峰在做什麼,
愛護自己現在居住的地方,也認同這個社區,
讓「永續」能夠擴及到每一個家庭,
深植每一個人的日常。 -
View More 「原」來性別是那樣─從原民文化傳承,看見部落的性別文化
-
View More  美PART 4 於光譜之上
美PART 4 於光譜之上美
美
文 /陳甜水
有次在高雄新崛江逛街,我拿著一件牛仔寬褲正要走進試衣間,突然被工作人員給叫住,「先生,那件是女裝喔。」當時的我頓了一下,「啊,好的。」說完便匆忙將褲子掛回架子上,快步走出店裡。當下我怎麼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因為男生不能試穿女裝,還是男生不該買女裝,如果不該,又是為什麼不行呢 ?
升上大學之後,我終於能一嘗大台北新鮮的空氣,上課再也不需要穿一身白淨的襯衫和卡其色長褲,世界彷彿宣布解嚴,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自由之身;大學校園如一場小型的時裝秀,從嘻皮、簡約到日式、韓式的服裝,應有盡有、日日上演。受到同學們的影響,逐漸我也變得喜歡購物,喜歡找朋友去西門和東區閒晃,右手抓一件新潮的外套,左手便要搭適合的長褲和上衣,看見喜歡的款式目不轉睛、躊躇良久已是常態,若看見紅標特價,總會倏地抓起來仔細端詳,有的直接丟進購物籃,有的則是在試穿完之後忍痛丟棄。
隨著時間過去,只要踏出家門的一天,我必然會在早上花十幾二十分鐘站在鏡子前,進行一場激烈的腦力激盪,在許多組合之間探求更多的可能性,拿下一件襯衫再抽出一件長褲,反覆將衣服摺好、掛起,為的就是將自己打扮得好看,而我在同學之間,也逐漸變成了他們眼中服裝較為「浮誇」的一位。有時會收到女同學的讚美,有時也被男同學稱讚很有心思和想法,但有的朋友三天兩頭便會朝我說:「你今天穿這麼正式要去哪?」、「今天要聚餐喔?」以為我精心的打扮是為了赴一場重要的約會;但我其實一直都只赴自己的約,每天都答應自己要整理好才能夠出門,要將自己打扮得美的原因,只因這是我相當喜歡的一件事。
圖源/freepix
這樣的生活當然不可能一帆風順,儘管在這樣美好的二十一世紀,已經有像哈利(Harry Styles)一樣主張無性別穿搭的大明星,有時候我仍會在全身鏡前躊躇不前,不確定是不是要多繫一條皮帶、將上衣紮入長褲,或是將棒球外套換成針織罩衫,讓自己身上的衣服和社會的普世價值有所衝突,但在最後一刻理性必然贏過感性:只要認知到今天會成為故步自封的一天時,我便無法強忍這般委曲求全,一定要將自己最想表現的一面展現出來,展現屬於我個人的美,展現不為社會上任何人所構築的美。
偶爾穿衣風格較為溫暖而柔軟,走在路上不免感受到其他路人的目光,此時我便想成是路人羨慕我的眼光和品味,當然,還包括了勇敢。於是我能不畏他人的想法,邁開步伐向前大步地走,霎時人行道和騎樓宛如香榭大道,風伴隨腳步往前吹起,呼嘯而過的車聲變成詩句,短根的鞋在地上敲擊回應,直到衣襬在斑馬線前落下至水平線,方才的一片風光才暫時從心裡淡去,等待幾十秒後再度碰見未知的奇遇。
穿搭對我來說就像是一件興趣、嗜好,更是一件我熱愛的事,從街頭風到簡約風,寬鬆到合身都是我的涉獵範圍,性別卻從來不是一件能幫我的衣櫃分門別類的一個標籤,一件卡其色寬褲應該放在長褲、淺色區,擁有溫柔、理性的特質,而不是將我變的較為女性;一件黑色大衣就應該放在深色、寬鬆的外搭區,擁有成熟、俐落的特質,而不是將我充滿男人氣息,從頭到腳,我穿衣的顧慮從來都只有色彩和材質的和諧,以及整體散發的氣質和風格。美不該因為性別而被限制,這些動人的特質也不單屬於任何一種性別,只要自己喜歡,那種美即便是誰都不能置喙。 -
View More  唱歌那件小事與「性別展演」PART 4 於光譜之上
唱歌那件小事與「性別展演」PART 4 於光譜之上唱歌那件小事與「性別展演」
唱歌那件小事與「性別展演」
文 /陳喬
作為生理男性,我的性別認同歷史中有兩條時間軸:
一條代表外於身體的,感覺的種種經驗疊加積累,軸線上的箭頭朝著社會化、「正常人」的方向指去。
另一條則潛在於身體,不可言說,是心靈與意識內容的加總,箭頭指向一個我真正的,或者想成為的模樣,無所謂正不正常。
兩條時間軸在認同歷史上,在我的身體經驗中,從聚合到慢慢地脫離彼此,平行,又不斷地嘗試縮短兩者的距離。
舉唱歌這個例子說明或許會更清晰。
在還未進入青春期,尚未變聲的九、十歲年紀,我總愛唱歌,唱女聲原音調的歌。
我還記得去庭園式KTV和大我五歲的姊姊對唱〈珊瑚海〉,總是我唱女聲、她唱男聲。隨後,青春期的到來如一把利刃,一刀兩斷地把這份美好切割開來,一半停留在姊姊身上,多年以後她的聲音依舊;另一半,即我男女莫辦的童音,則永遠駐留在過去了。
當然,渾然不覺的性別概念也隨即混入我青春期的性徵中,「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愈來愈像雙色的棒棒糖,千萬條細長的糖絲緩慢地被黏在一起,從此密不可分。
青春期前我總唱S.H.E.或張惠妹的歌,沒有人有意見。
變聲後聲線逐漸低啞,歌聲總像蓋上蓋子一樣悶悶的唱不響亮,在KTV點女歌手的歌也逐漸被視作不正常,家人、親戚、朋友都問:「為甚麼不點一些周杰倫、羅志祥的歌?」我說音太高唱不上去,他們能接受;我說不喜歡,他們就納悶了。男生怎麼都盡唱嗲聲嗲氣的歌?為什麼不聽男歌手的歌?我猜想他們心裡充斥著這些問題,只是基於很多原因不問出口。
圖源/pixabay
回到認同史的角度看,變聲這個性徵似乎象徵兩條時間軸的初次分別,青春期捉走童音,卻沒有連著我喜歡的、想擁有的歌聲一起帶去。
隨著性徵愈來愈突出,那顆應該視作男子成熟象徵的喉結,對我而言卻是噎在喉頭的一顆毒果實。可是與此同時,不把它吞下去才是「正常」的,如同社會化過程聽見其他人說的「男生不能愛哭」、「男生要有擔當,有肩膀」等話語,沉重,卻仍要聽從。
在大學以前,我從一個拿起麥克風那麼自信的小毛頭,長成一個喉結明顯的少年,年過一年拿起麥克風的姿態卻愈加退縮。
有幾次亟欲得知自己歌聲是甚麼樣子,錄下自己的歌聲,放音時一個全然別於我的想像的低啞歌聲從手機跑了出來,如同一隻怪物站在面前。我害怕地不敢面對,選擇忽略,那之後再也不敢主動和其他人去KTV。
我明顯地感受到兩個時間軸分離、甚至疏遠的關係,卻也承襲青春期以來的社會性別概念,以至於羞愧感隨時間愈加明顯;對外保留地稱自己不愛唱歌,對內卻覺得自己唱歌難以入耳,害怕歌聲裡那隻怪物再次出現。
大學時重拾唱歌的自信,最大的契機是蘇打綠的主唱青峰和張懸。兩個歌手巧合似地顛覆青春期後我對男女歌聲的認知,前者音調高而輕柔;後者音調低而沉穩,我在兩個倒過來的極端中重塑自己的歌聲,過程中不停反思聲音、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關聯。
那一陣子發現自己唱張懸的歌總用男性化的口吻,唱蘇打綠的歌聲音則會偏陰柔。
或許是這一點讓我逐漸體驗到如同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所說的「性別展演」概念。
這個概念簡單地說,就是
性別可以被行動演繹,能像穿衣一般自由地去選。。
唱歌的特定口吻與聲音表現,對我而言就像在展演性別。兩位歌手又讓我意識到,生理性別並不侷限展演。
而長期以來把生理性別當作行為依據的我,在自我內部製造出了矛盾,亦即:明明想唱出陰柔的女聲,生理男性的身分卻使我不能選擇這種屬於女生的行為。
這個發現使得兩條徬徨不定的時間軸終於重新彼此牽引──關乎正常與否的社會化軸線與追求自我的軸線之間,經歷了從青春期起的矛盾與平行的長期狀態,又一次地開始聚合了。
-
View More  生理男的發育心事PART 4 於光譜之上
生理男的發育心事PART 4 於光譜之上生理男的發育心事
生理男的發育心事
文 /梗好
十二歲,小六的那年,生理男都經歷怎樣的發育心事呢?
那一年,可能因為雄性激素開始作用,我的聲音從高高細細的童音,開始變得粗啞,在走廊奔跑嘶吼的日子裡,我常常不小心在尖叫的過程中破音,就好像失敗的演唱家一樣,得到的總會是同學們的指點與嘲笑。
也是在那一年,我的嘴邊開始長出薄薄的細毛,我光滑的小腿跟手臂,開始爬上黑黑的毛髮,同學們都說我看起來好像黑猩猩。
升上國中的時候,可能我並不是那麼陽剛,不符合國中男孩子想像中的男子氣概形象,我的皮膚不管怎麼曬總是曬不黑,我手臂與小腿的毛髮越發茂盛,因此我最討厭的日子,就是夏天體育課,被要求一定要穿短褲上課的時候。
從冬天轉換到夏季的日子裡,我的皮膚經過一個冬天的衣服覆蓋,再穿上短袖與短褲的時候總是白皙透亮,但在又白又纖細的肌膚上,居然覆蓋了一層厚厚的黑粗毛髮,總是在我全裸站在鏡子前面凝視自己的時候,深深的討厭那樣的自己。
同學們總是說:「他的毛好多,在他的皮膚上看起來好違和喔。」或者直接叫我白皮猩猩,於是手毛腿毛變成我發育時期最自卑的記號。
我曾經問過我的健康教育老師,為何我的毛那麼多,然後為何我的皮膚那麼白?
老師總是跟我說西洋的男明星都是那樣,很英俊、很陽剛、很受到崇拜,只是當時的我完全無法享受到父母親口中的陽剛男性紅利,反而因為我的生理外在,變成眾人嘻笑嘲弄的對象之一。
圖源/freepix
那段發育的日子裡,只要能夠穿長褲我就不可能穿短褲,甚至因為擔憂要在同學面前更衣、睡眠,而拒絕參加國中時期的隔宿露營。
升上高中的時候,我的身型抽長長到接近一百八十公分,我發現我的骨架比起同齡男性寬大,我的鬍子顏色也是黑棕混雜,我的髮色在沒有染燙的情況下變成棕紅色,一瞬之間,我的身體居然奇妙的組合出許多原先不存在的性徵,直到我深入詢問我的家人,我才知道原來我的高祖父是荷蘭人,我的血脈裡留存著百年之前他的性徵,這些埋藏在家族成員血液裡的遺傳因子,在我的身體卻是奇妙的展現出來。
我在青春期的末期,得知我基因深處的密碼,才終於知道我與同儕的不同之處。
發育期的我並不能認同自己的身體變化,對於同儕的嘻笑與遊戲,我將之聽成嘲弄的詛咒,直到我釐清我家族的遺傳軌跡,我才知道其實生理男性不只有單一的形象,生理男性的外貌可以很多元,這些都是基因的秘密,也是家族血脈的祝福。
於是我開始穿起短褲,在炎熱的夏天裡,不再將自己的身體束縛在長褲之中,開始勇敢嶄露我身體原本的樣子,
因為我終於知道沒有一具身體是應該被嘲笑、排斥,被輕蔑的對待。
朋友常常羨慕我皮膚白皙,我總是會告訴他們原來的樣子最好看,那具最初始的、傳承著百年血脈與基因的身體,都是美麗又受到祝福的身體
-
View More  婆媳關係的進化版PART 4 於光譜之上
婆媳關係的進化版PART 4 於光譜之上婆媳關係的進化版
婆媳關係的進化版
文 /柴犬菸酒生
這是的,我是一名男同志。男同志的這個身分,嚴格上來講是從國中起開始陪伴著我的各式成長──包括高中異男忘、大學開始使用各種交友軟體也建立起同志認同,而到現在我與我的另一伴交往了三年多。而在同志身分之外,我也同樣自認為是一名女性主義者,無論是在研究所的學術研究、或作為一名家暴防治社工,更包括在日常生活上的實踐。性/別的概念在我的生命經驗中是緊密相連的,而在學院的理論訓練之外,給我在生命中的滋潤,是我的家人、我的伴侶與朋友。
我在上大學的那個暑假正式向我的母親出櫃了。
也許是因為我的個人特質蠻符合社會對於男同志的刻板印象是陰柔的,或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她早已開始做下心理準備,出櫃的剎那並沒有那些在腦海裏面試演無數遍的家庭戰爭。
到了後來,我的母親某次和我炫耀她看了某位性諮商師的文章,我才知道雖然她因為過往的生命經驗而足夠開放與接納她的小兒子喜歡的是男生,可是她還是需要人告訴「男同志是怎麼一回事」,才不會因為恐懼而將與她親密的小兒子拒於千里之外。
在2018年的公投裡,在某次周末回家與母親聊天的過程裡,她和我說了家裡附近的菜市場有人在宣傳愛家公投。
我其實也不意外家裡附近有支持愛家公投的群眾,
但使我出乎意料的是我的母親──她說她那天上前去反駁愛家公投的人,質疑他們、並說「同性戀不是病」。
我一直都以為母親是接受了我的性向,但會放在心裡而已──沒想到她站出來了,我始終感動於她的勇敢。
但我的母親並不喜歡我的男朋友。我和男友的認識是透過交友軟體,那時他正在我的家鄉當兵、而我則還在台北念大學。在我二十歲生日那天,我們決定交往了──其實我們之間相差了四歲,但是因為對於生活有著相近的目標和價值觀,我們的磨合期很快地就結束了。
到目前為止聽起來就是「很一般」的交往,可是當我們倆的性別相同時,交往的過程就增添了幾分緊張感。
圖源/freepix
從高中二年級開始,身邊的人們幾乎都知道我的性向,在大學期間我也參與在性別與同志運動中;對我母親來講,出櫃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幾乎是扛下了這個社會為數不少對於同志的惡意與歧視──可是我的男友並沒有出櫃。我的男友是一名深櫃男同志,他是家中獨子、父母極度地不支持婚姻平權,生長的環境也不似我幸運地遇到包容與支持性別平等的朋友們。
面對他的不出櫃,我也曾經因此對於這段關係迷惘過:「他沒有出櫃、沒有公開我們的關係,這樣他到底愛不愛我?」但因為大學的社會工作教育與在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實習的經驗,我知道他也同樣迷惘──對於性向的疑惑、家庭關係的衝突,以及周遭友人的眼光──這些都是他的世界,我並不希望他的世界因此崩毀。
如果出櫃與否真的能構成一個人愛著另一個人的證據,我更希望他能夠在舒適自在的環境中生活、並且將我放置在他做下的每個關於未來的決定裡。
而我雖然也無法和我的母親以那些性別壓迫的理論觀點,說清楚那些無法出櫃背後的生活考量,但我想我的另一伴是會願意用他的接下來人生,向我的母親保證會對我好──
生為同志並不悲慘,也同樣會被愛著
性/別雖然作為一種社會分類的基礎與學術研究的領域,我與母親、與男友的親密關係,也因為同志身分這樣的性別概念而交織在一起。
但在這篇記錄中,我想陳述的是:
好的性別經驗並不是全然地以各式反壓迫與批判的理論,
或是激烈地衝撞社會去建構一個烏托邦,
而是能實際地在日常生活中逐漸走出溫柔革命。 -
View More  我的日常性別經驗PART 4 於光譜之上
我的日常性別經驗PART 4 於光譜之上我的日常性別經驗
我的日常性別經驗
文 / Rita Yu
這些年在南投的個人生命經驗似乎與社會倡議無法切割。我身上常配戴彩虹系列裝飾物,是因為自己女同志的身分在這塊土地被漠視、被排擠、被攻擊,承受的壓力讓我更勇敢的想要跟這個社會對話,希望與他人思想交流。
像是2017年某天,等待伴侶下班時我到巷口買水煎包,老闆熱切地問我「下班時間急急忙忙的要去哪裡?」我說:「等等要開長途車北上籌辦婚禮,所以買些糧食車上吃。」
對方的暖心讓我願意坦承告知自己的性向,我與伴侶為何不在南投辦婚禮,為何無法在家鄉公開我們的關係,解釋現今社會對性少眾的扭曲價值,沒有法律作依靠的伴侶關係是如何脆弱。
當談完彼此對婚姻平權法案的看法後,老闆語重心長的說:「謝謝你跟我講這些,因為我是第一次跟活生生的同志聊天,我沒有接觸過同志朋友,對於同志的認識都是從影音媒體來的啦!」
南投人口漸漸老化,我認為長者的思維若開始變通,世代間的隔閡就有可能化解。
圖源/freepix
我曾到農產特賣會擺攤,到中老年人的場合對話,大家賣百香果、鳳梨,而我賣理念。隔壁攤販大哥好奇我攤位的彩虹旗幟前來詢問,我解釋性平教育,也說明彩虹所代表的多元含意。大哥很自豪的說對兒子的性教育觀念在街坊裡是最開放的,分享他在鄰里間找不到相同教育態度的家長可以討論的窘境。
還有一位擔心兒子是同志會得愛滋的媽媽來聊天,釐清自己的疑惑。即便他們起初對於性別的觀點不太正確,但我深刻地體會到他們也需要性別友善的同溫層,才能放心地把擔憂或觀念與人分享並被傾聽。
因為工作需要我常到圖書館借閱跟性別有關的書籍,館員們對我都很熟悉,常跟我討論一些與性別有關的社會輿論或新聞,像是同性婚姻制度、通姦除罪化、情慾流動、外遇、形式性婚姻等話題。這些互動都讓我好想在圖書館開讀書會, 邀請大家一起來談性說愛呢!
我的日常總是在充滿二元刻板樣貌的社會裡掙扎,如何在以男性為主體的架構下看見女性與其他性別的需要,是我每日都在經歷的挑戰。
就算與家人觀賞影片,我的性平雷達常常嗶嗶作響,例如電影【大餓】1 描述社會的主流價值框架了女性的身體意象,也否定了一位想著裙裝的男孩對自己的性別認同。
劇中的一句消極思維台詞『推翻改變世界太難,不如改變自己比較快』
讓我回想起一個在南投認識的胖女孩,曾被網路輿論無情的批判,在現實生活中被排擠,最後她只敢躲在鍵盤後生活而不敢面對真實的社交關係;小男孩穿裙裝的情節也讓我想起在南投舉辦的活動中,曾陪伴跨性別孩子找尋真實的自己,陪伴 Ta們渡過被言語辱罵所產生的自卑感,並找尋更多性別友善的支持系統幫助 Ta們遠離傷害。
在南投的這幾年,每當我提起自己有同性伴侶的時候,總會被問 「那你是關係中的男還女?」這讓我聯想起與朋友一同追的戲劇 【帥 T 空姐】2,我總是用酷兒化的經驗去反駁女同志圈裡不成文的 T/P 文化。 一般人總認為女女相戀的互動中得要有人像異性戀裡男性角色 T (Tomboy - 假小子),還要有人要扮演女性 P(婆)的角色 (Tomboy的老婆),這些都像極了父權思維的伴侶關係。P(婆)就像是 T 的附屬般地存在,像許多男性公眾人物的太太們總被忽略自己的獨特性一樣,這些迷思也是我嘗試打破的刻板印象。
這些生活經驗,是因為性平之眼被打開才看的見,還是這些日常開啟了我從不同視角看見性別呢?不論是因是果,
我都感激生命中的特別經歷,才能更勇敢且柔軟的心面對人生的挑戰與困境。
備註:
1. 【大餓】2019年臺灣電影,一部性別與身體認同有關的作品。描述體態肥胖的主角受盡歧視,決心透過減重改變自己,重新找到自我的過程。導演:謝沛如
2.【帥 T 空姐】2019年臺灣原創戲劇,探討職場性別議題,點出生活與職場上性別不平等的困境、性騷擾、言語騷擾、性向歧視等議題。導演:周美玲 -
View More  謝謝你相信我PART 4 於光譜之上
謝謝你相信我PART 4 於光譜之上謝謝你相信我
謝謝你相信我
文 / ㄗㄗ
還記得我在國中的時候,我是不太能接受同志的,覺得婚姻應該要一男一女,才可以有後代,人類才可以繼續存活。
直到有天,有個朋友跟我出櫃,才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跟他會認識說來有趣,剛開始我對他的印象不是很好,覺得他十分喜歡捉弄人,不過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我跟他變得十分要好。要好到我明明不喜歡同志,他還是跟我出櫃了。
在後來的某天,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在上電腦課,因為只有電腦課的自由時間我才可以用臉書和朋友聊天。那天,他忽然問我「會不會覺得同志很噁心?」,我說「有時候同志會令我有點反感。」,他又問我「如果朋友是同志呢?」,我回答「應該不會吧。」不過當時我也不敢篤定真的不會。幾分鐘後,他跟我說了他是同性戀,我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問他他是不是一時錯掉了。後來的我真的覺得這個反應十分差勁,不知道他天人交戰多少回才跟我說他是同性戀,可是我卻是這個反應,虧我還是他的好朋友。
在他跟我出櫃後,我反省了自己,同性戀是哪裡錯了嗎?為什麼連最基本的我喜歡誰都不能被接受?許多問題衝擊著我,也讓我開始思考「喜歡上同性」真的是不能被接受的嗎?他猶豫不說的感覺讓我十分心痛,為什麼他無法在我面前做真實的自己,因為我的原因,而讓他不能真正的說出自己真實的感受,想到這裡我非常難過。之後我也漸漸可以同理、理解我朋友,不論喜歡什麼性別都沒有對錯,勇於追求自己所愛,是很勇敢的事情,不應該被否定。
圖源/freepix
高中之後對於「性別友善」也更加了解,大學後也因為修了有關性別的課程,讓我更加了解「性別」的概念,藉著這些課程,也反思了自己的經驗,發現到自己有關性別的經驗也有些不同,我不喜歡被「男、女」這種性別二分框架框住,我的性別認同一直不是很固定,性傾向也是。
現在的我覺得喜歡什麼人、認同自己是什麼,其實都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自己舒服自在就好,因為是自己的人生,自己快活是十分重要的。並非說他人的言行舉止不會影響到自己,而是因為要在意所有事情在意不完。雖然用說的是很簡單,但實際要這樣想是有難度的,我也正在「可以好好接納真實自己」的這條道路走著,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走到終點,但我想只要正在走,總有一天可以走到。
你呢?走完了的話,恭喜你,我好羨慕你已經走完了。如果還沒開始或走到一半,沒關係,我們可以一起出發、前進,往接納真實的自己共同邁進。過程中會有許多拉扯跟質疑,可是不要緊的,這是必經之路,因為這些可以讓自己更加了解自己。
記得請不要厭惡自己的認同,因為我們並沒有錯。